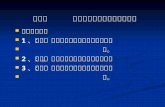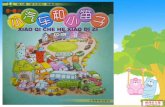诗/ 绪/ 纷/ 飞...
Transcript of 诗/ 绪/ 纷/ 飞...

人/ 文/ 情/ 怀
唐代诗人贺知章有一首妇孺皆知的诗《回乡偶书》,坐在重庆至营山的动车上,不由得想起这首诗,万千思绪涌上心来,让人难以平静……
我的先生是四川营山县人。为了上学,1948年他离开营山,和三个姐姐一起,跟随守寡的母亲到重庆投奔舅舅,栖身在一间小屋中,当时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1956年,先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青海一所高校教书,我和他就是在青海高原相识并结为伴侣的。结婚前,我们计划到四川旅游,顺便到营山拜见亲友。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
尽管双脚未曾踏上营山的土地,但先生对故乡的描绘还是盘桓在我的脑海里:仅有一条瘦削的直街穿城而过,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没有机动车,只有颤颤悠悠的滑竿。如果步行,从街头走到街尾,也用不了半个钟头。不过,先生描述的营山小吃味道独特:营山苕粉、凉面、腱子牛肉、油茶馓子、羊肉米粉、大汤圆……让我馋涎欲滴,很想到营山亲口尝一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全家迁居重庆,我几次提出回营山认祖归宗,但先生总是不积极,回乡的小船一直搁浅未能起锚。眼看20多年又过去了,我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在儿子和女儿的一手张罗下,“寻根之旅”终于提上了日程。
当我们一行四人走出火车站,踏上原本应该熟悉,但此刻却陌生的土地时,营山的朋友肖卫兵早早在出站口迎接我们了。还有一位是南充女作家邹安音,她和我仅有数面之交,却亲如家人,特地从南充赶来陪我们。
坐在车里,先生惊讶地问:“这是哪里啊?马路这么宽!”我从车窗向外望去,宽阔平坦的双向四车道,一幢幢崭新的楼房从眼前掠过,花坛、草坪、绿树、华灯组成了一幅幅色彩缤纷的画面。路面干净整洁,完全是现代化城市的格局,哪里还能觅到“一条直街”的踪影!经朋友介绍才知道,营山已经是“国家级卫生县”了。
晚上,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去品尝营山小吃。闻讯赶来的营山作协主席李建春带我们去小吃街。先生看到小时候爱吃的“营山苕粉”“营山凉面”,笑逐颜开。安音反客为主,直往每人碗中捞面。前不久,我从媒体获悉,营山举办“万人吃凉面”活动,场面十分壮观,据说已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饭毕,大家一起去中央公园看夜景。夜幕笼罩下的中央公园风姿绰约,那曲折迂回的湖上栈桥,那璀璨瑰丽的束束灯光,那悠扬曼妙的音乐喷泉,构成如幻似梦的意境,让人产生飘然欲仙的感觉!更让我们赏心悦目的是,那一片宏阔的湖水在夜色中闪闪烁烁,明明灭灭,似无数星子在跳荡,又像一池碎银在发光,带给人无限的遐想……
既然是“寻根”,自然要寻找祖屋和儿时玩耍过的地方。次日在肖卫兵的带领下,首先来到了白塔公园,膜拜这座建于道光年间的回龙塔。在先生的记忆中,白塔离城很远,荒草遍地,而今白塔公园已是城市中心。整洁的石阶,成排的绿树,焕发出勃勃生机。白塔高达九级,在单数的塔层上都嵌有横额,诸如“威震山河”“光耀紫极”“文运出海”等。最底层还有一副楹联:“砥柱回澜波澄朗水;奇峰拔地秀启绥山”,对仗工稳,遣词考究,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站在巍峨的白塔下,肖卫兵给我们讲起这样一个传说:营山地形酷似一艘大船,可谓风水宝地,但古代并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当地的人才也走不出去。杨尚容来营山作县令期间,多次站在县城的制高点观察,终于有所感悟:虽然县城形似船舫,东西南北均被两条河围绕,但缺少一根桅杆,这艘船只能停泊在太蓬山下,驶不出川。于是,决定在城东梅家梁上建此白塔,给大船竖起“桅杆”。塔建成后,仅明清两代就出了几十名进士,民国年间又有11位营山学生,于1919年至1925年先后去法国留学,其中就有我先生的父亲黄知风。
离开白塔公园,我们沿着宽敞的马路,奔向老东街寻找当年的祖屋。但这里变化太大了!灰黑低矮的旧式民房早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完全找不到归家的路了。附近的盐市街、纸市街、刘二桥等虽还留有一些残存的痕迹,但也早已不是昔时的模样。先生回忆,儿时家里有一个后花园“西园”,曾经有荷花池和一片桃树林,他父亲本打算种上大片果树,搞成一个果园。但还没等计划付诸于实践,死神却突然降临,刚刚40岁的黄知风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四个未成年的子女,撒手人寰。当年公公是因为去南充乡下赈灾,不幸染上了霍乱,这种病在当时无药可治,不仅自己英年早逝,而且搭上了最小的女儿。我先生也被传染上了,幸亏他命硬,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婆婆含辛茹苦,将四个子女拉扯成人,后来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亲友都非常钦佩这位母亲,给予她很高的评价。
这位贤惠而又坚强的母亲,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亲眼看一看营山的新面貌,亲身感受一番改革开放40年的新变化,该有多好啊!好在有当地东道主的热情引领,我们代她叩访了昔日故园,探寻了旧时街坊,找到了失联多年的亲戚。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后辈找到了自己的根脉,这些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双亲了。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荣誉会长)
在先生的记忆中,白塔离城很远,荒草遍地,而今白塔公园已是城市中心。整洁的石阶,成排的绿树,焕发出勃勃生机。
诗/ 绪/ 纷/ 飞
乡/ 村/ 故/ 事
打莲枪
葡萄园之夜(外一首)
谭萍
邢秀玲
我小学时,那年正月初三,头天晚上父母同意我去走我喜欢的亲戚,所以起得很早。刚吃完早饭,换了新衣穿了新鞋,拿好父母准备给亲戚的礼信,要出门,就听见院坝里有人在唱,还有节奏的拍打声。
我们的院子五户人家,先是小孩出门看,后来是大人们出来。有端碗正吃早饭的,有拿着梳子正梳头的,还有提了猪食桶的,都站在屋檐走廊上看院坝里的热闹。院坝中有三个残疾人,其中两个盲人各手持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竹竿上稀疏地缠有红布条,两头钻有孔,各套有几个铜钱,两头的顶端,有合适的飘带。两个盲人舞动竹竿,每一杆都拍打在自己相关的部位,竹竿两头的飘带,随舞动幻出好看的风采。他们嘴里唱着,手里舞着,边唱边舞,舞和唱极尽喜庆。像是刚杀了年猪,贴了对联,丰衣足食,一切都如人愿
我爸说:“打莲枪的好早,他们不容易。你去给他们舀一撮箕米来再走亲戚。”听从父亲的,去米缸舀了米,那个脚残的上来用口袋接了,道了谢。只听两个盲人换了音调,突然就高亢起来,手里的竹竿舞动的频率也快起来,竹竿两头的铜钱发出欢快的声音。顿时,整个院坝被两个盲人舞出了热烈,一改渝西正月还有的寒冷,仿佛春天的盛大,春阳温暖,万物向上;又像夏日,庄稼正旺;更像秋收,田间地头,欢天喜地。
我走亲戚回来问父亲:“我走那天那表演的,叫啥?”父亲说:“这就是莲花落,在我们这个地方叫‘打莲枪’。残疾人对生计的付出要艰辛于正常人很多倍,所以他们也沿袭发扬了打莲枪。每逢过年过节,他们就出门给人表演,表演过程中也向观众讨要些彩头,来改善生活。”父亲又说:“他们多以祝福的形式给大家表演。其实他们对世间的悲喜深入三味。别看那天早上他们跳得唱得那么欢,他们只是把生活的痛藏了起来。我看过他们深得道行的表演,既能唱出花好月圆,更能舞出沧海桑田。”父亲说完就去忙他的活路去了。
一直读书,从初中,到高中,最后是离了老家。等我再次安静下来,就越想老家,更希望老家的枝丫在我身上延展,再从我的血脉,一直生长。
城市是极少见打莲枪的。只是偶尔去乡下,在某处能听到铜钱啪啪作响的节奏和唱腔。今年端午回老家,在老街上看民俗表演,其中就有打莲枪。他们已经演义了以前的组合,变成了一队身体健康的人共唱共舞,衣服也喜庆光鲜。他们的唱腔干净,美好,敲打的舞姿也整齐有韵;五月的天空被他们唱得亮丽深邃,一条沧桑的老街被舞得生机盎然。
回程里,我的脑里全是打莲枪的唱腔和舞姿,不自觉地就张嘴唱了起来,挥舞着虚拟的竹竿先敲打地面,然后是脚踝,膝盖、手、肩、背、各处关节,像那些真正打莲枪的舞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他们的唱腔干净,美好,敲打的舞姿也整齐有韵;五月的天空被他们唱得亮丽深邃,一条沧桑的老街被舞得生机盎然。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年8月11日 星期六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钟斌 美编 朱艳春制图 朱艳春 责校 李勇强 朱艳春
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夜雨两江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黄海子
七十春秋故园情
夜幕降临一切都安静下来
我开始修复自己把白天散去的养料和水分散去的甜统统找回来
从根茎、叶子、空气、土壤从一切能给予我的介质里摄取营养重新排列分配酝酿
经历过修剪枝蔓的苦痛蚊蝇的叮咬与麻雀的偷袭所有烦恼的细节我都当成一种考验在夜色中消融日复一日就这样慢慢成熟
天亮之前我将离开藤架把鲜活的汁液饱满的珍珠玛瑙一般的最好的自己送到你面前谈一场酸酸甜甜的爱恋
紫藤花下
墙角的紫藤开花啦不声不响转眼又是三年
种花的时候你说这花好养活给它一根树枝就能往上攀
如今繁花盛开音犹在耳你却渐行渐远
想你最好的方式就是独坐紫藤花下续上陈年老酒把欠你的那弯新月那把胡琴全部请出来
满园青雾里杯双人单用什么来碰响咿咿呀呀的思念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