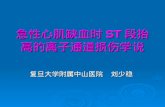新时代:文学更加神圣 -...
Transcript of 新时代:文学更加神圣 -...
春节将至,好朋友送来一套纪录片
《过年》的光盘,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塞进电脑
的光驱,细细地品味起来。炉灶里燃起红
红的灶火,饭锅里冒出升腾的热气,瑞雪中高高挂起了红灯笼,孩
童们燃放着长长的鞭炮……这些象征着过年的物象在镜头里反
复闪现,一下子就让我沉浸在对小时候过年情景的回忆之中。
收割、打场、卖粮、拉粪,忙完这些活计,就已经到了小年,
从这时候开始,农村社员们便可以放下生产队的活计,准备自
家的年货了。我们生产队效益长年不好,一天挣10个工分,每
个工分只值几分钱。社员们辛苦劳作一年,勉强能把家人的口
粮领回家,拿到现钱是多年没有听说的事情了。家里养的鸡鸭
鹅猪,只能换回从来不敢任性使用的油盐酱醋,再偶尔给孩子
们买件新衣服,日子年年紧紧巴巴地过。过年,是个处处都要
花钱的时候。家庭妇女裤腰里薄薄
的毛票禁不住花,只好处处节俭,能
省就省。
既要省钱,还要把年过得热闹,社
员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在我13岁那一
年,刚吃完小年的饺子,父亲就穿上靰
鞡,打上绑腿,戴上狗皮帽子和棉手
套,让我坐在爬犁上,轻快地向山里进
发。路过河边的时候,霜雪凝成的树
挂层层叠叠地挂在老榆树上,被风一
吹,便片片飘落,在朝阳的照射下放出
金灿灿的光芒。我们的任务是掰干
枝,就是树上枯死的枝条。进了树林
之后,父亲就放下爬犁,抄起安着长柄
的镰刀,向高高的树梢张望,看到枯枝
就用镰刀钩住向下拽,一声脆响之后,
长长的干枝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忙
活了整整一天,父亲的帽子摘了,手闷
子甩了,连冒着热气的棉袄也扔在了
雪地上。当日头偏西的时候,爷俩儿
吃力地拉上满载的爬犁奔家了。过年
的时候需要蒸煮的东西多,家里也要
烧得暖暖和和的,这一天的收获,足可
以让大正月的家里灶火始终兴旺,舒
舒服服地享受热炕头带来的幸福感觉
了。“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大肉;二十七,杀小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玩一宿。”父亲拉着爬犁,兴致十足
地给我念起这套过年嗑儿。
第二天一早,我不再跟随父亲上山,而是约上同学小志,在
爬犁上装好冰钏子和抄网,13岁的我们雄赳赳地到大河去冬
捕。找一处背风的河湾停下,急不可耐地开始轮流打冰眼,之
后把抄网通过冰眼伸进河水里不停地转动。冰层下面的鱼儿
们因为缺少氧气,一嗅到冰眼透进的空气,便一窝蜂地跑来吸
气,也就中了我们的道,统统被抄进了网里。收成超出家里所
有人的想象,我和小志晚上回到家里之后,每人分到整整一面
袋冻成棍的各种鱼。妈妈面带喜色地把其中个头匀称的鲇鱼
挑出来放到一个饭盆里,第二天一早就端到大队供销社门口去
卖。下午妈妈拎着空盆、捧着一叠报纸回来,我得到几毛钱的
奖励。“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妈妈的骂声还没落下,我已
经攥着钱跑出了家门。在供销社里买了一连二百响的小鞭、两
个往年只能看不能买的嗤花,再把剩下的钢镚儿换成糖块放到
嘴里,夫复何求地回家吃猪肉炖酸菜。
吃完晚饭,父亲把平时用的25度灯泡拧下来,换成60度
的,屋里一下变得亮如白昼,我和弟弟妹妹顿时高兴得欢呼起
来。接着父亲去打糨糊,和妈妈用报纸糊墙。报纸是农民家中
糊墙的首选,最重要的是成本最低,对我来说,没事儿的时候就
可以看上面的内容,有文字的日子过得快。“儿子快来看看,这
报纸咋还有错的地方呢?”只上过两年学的妈妈边往墙上粘报
纸边问我,我也好奇地赶紧凑上去。“你看看,这北京怎么落了
一个北字,变成了京字呢?”“这哪是错了啊,北京就简称京”!
我有点不屑地转过身去。“还是多上学好吧,大儿子比妈妈懂得
多了!”妈妈笑着说。我家的泥草房不是很大,十几张报纸就糊
满了。在黄色电灯泡的照射下,满屋充满了喜气洋洋的金色。
父亲坐在炕头上抽烟,妈妈下地去炒瓜子。“雪苫的房,雪白的
墙,屋里挂着毛主席像……”欢快的歌声从外屋传进来。
家里日子紧巴,妈妈每年都在猪肉上省,今年全家六口人
只砍了10斤猪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妈妈一边切割
刚买来的肉一边说,“走在外边,谁也不知道你肚子里装的什
么,可是少买几斤肉就能添件新衣裳,穿戴齐整了过得才像日
子,才没人笑话你。就连有钱的城里人也都这样过日子,你们
没听说他们是的确良的裤子,苞米面的肚子吗,道理是一样
的。”这样一说,我们兄弟姐妹再有意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肉少自己再想办法。吃过早饭,大人孩子都走出家门之后,
自家的小院里静得可以罗雀了。我和弟弟来到院子里扫雪,之
后从仓房里搬出筛子、稻草和稻粒儿,用一根拴着长绳的木棍把
筛子的一个边沿支起来,再往斜扣在地上的筛子里塞入碎稻草
和少量的稻粒儿,拉着绳子进屋,躲在门里向筛子处张望。那个
时代麻雀出奇的多,这种与人争食的鸟儿也是人人喊打的四害
之一,所以逮麻雀可是既解馋又不讨人嫌的好事儿。麻雀眼尖,
看到筛子下面的吃食,不一会儿便叽喳叫着蜂拥而至。但麻雀
可不是好对付的主儿,刚落到地下,它们只在筛子外围蹦跳鸣
叫,眼睛不时地向四周张望,偶尔有个胆子大的,突然钻到筛子
下面,叨起一个稻粒儿后马上退出来,根本不给我们拉绳的机
会,把年幼的弟弟气得直跳脚。再过一会儿,麻雀们实在看不出
危险,才有几个先钻进去,之后院里所有的麻雀生怕落后了没食
可吃,便从四面八方一起涌向不大的筛子下面。我和弟弟拉住
绳子使劲一拽,同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奔出去把准备好的破鱼网
罩在筛子上,把麻雀一个一个逮出来。妈妈最喜欢做咸黄瓜炒
麻雀,我们哥俩用一个上午就把主料备好了。
越到年根儿,大人小孩就越得空闲了,大家纷纷聚成各种
“群”,做共同喜欢做的事儿。到了晚上,我的最大爱好是去谷
老师家听他讲古。谷老师是城里下放的五七战士,听大人说原
来是在大学里教中文的老师。受他的影响,我才在高考的时候
把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中文系。喜欢听讲古是不分年龄的,每晚
谷老师家都挤满老人小孩和刚忙完家务的妇女。谷老师讲《三
侠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每当讲到情节的紧要处,他都停
下来吭吭咳嗽几下,把听客急得直搓手心。这时候总有人或者
递上一块糖,或者捧上已经在手里
焐热了的冻秋梨,谷老师倒不贪吃,
含上糖或者啃两口梨便接着开始,
直到半夜三更,大家才恋恋不舍地
回家睡觉,梦里全是秦琼卖马和呼
延庆大上坟的情景。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转
眼之间大年三十到了。天一擦黑,
父亲就把家里的灯泡由60度增大到
100度。在亮堂堂、热烘烘的家里,
父母忙着剪挂签、贴福字,姐姐妹妹
们聚在一堆玩嘎拉哈,我和弟弟把
鞭炮从被摞下掏出来,十分小心地
进行分类,之后摆在柜盖上待用。
做完屋里的活计,妈妈便起身去灶
屋炒菜,父亲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开
始和面包饺子,手里忙活着,他给我
们讲起了李闯王的故事。
酒菜上桌,饺子下锅。这时候
我和弟弟便急不可耐地各自点上一
支烟,拿起鞭炮冲到屋外。先是把
成串的鞭炮挂在木障子上点然,闪
烁的火光中发出连串的脆响,接着
燃放缤纷的嗤花。放完自家买的,
余兴未尽地向村里望去,到处是鞭
炮的响声,到处是礼花在空中的造
型。光亮和脆响,这是平日里农村最稀少的东西,看到了听到
了,才更真切地感受春节来临,把热闹和喜庆推向最高峰。煮
好饺子,父亲先用饭碗装上几个拿到屋外,虔诚地放到窗台上,
他用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方式向神灵向先祖表达自己的敬意。
回到屋里,姐姐妹妹们已经换上新衣服,我和弟弟没有添
置新衣,不情愿地换上妈妈递过来的新袜子。等全家人都围坐
到饭桌前,妈妈一声令下,大家便纷纷拿起碗筷,尽情地享受一
年的收获,享受合家团圆所带来的难以掩饰、难以言表的快乐。
时光荏苒,转瞬之间40年。父母已经仙逝,兄弟姐妹也都
纷纷离开,就连家乡的村庄,都因为连年水灾而搬迁到了远处
的山坡上,当年生活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回想起来,经过
40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不是当时的样子,可以说,现
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比当时过年的吃用也要好得多。但我们为
什么还对当时的过年情景难以忘怀、年纪越大越思乡心切呢?
我觉得我们怀念的,应该是那份独特而浓烈的乡情、亲情和友
情。一个天气现象、一个电视剧情节、甚至天空飘过的某种气
味,都能联想到故乡的一段往事,让人久久不能释怀。这种感
觉就应该概括成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词语——乡愁。
每周四出版 本期出版2018年2月1日
周刊 DONG BEI FENGEmail:jlrbdbf@163.com
一岁一枯荣,2017年和2018年击鼓传花般自然而
贴切地连接到了一起。进入新时代,当然要有新风貌,
就是要在充分认识新时代特质的基础上,让文学焕发出
新的精神风采,突然想起著名作家陈忠实那句名言:“文
学依然神圣”。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痛苦之极的鲁迅曾这样长叹。与鲁迅相比,我们何其幸
运,躬逢盛世,只管在文学的田地里快乐地耕耘,种植梦
想,民主与自由的风荡涤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任务非常
明确——保留文学物种。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写下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
大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汪曾祺也说过:
“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文学虽然不能生产粮食,不
能盖高楼大厦,但能润物细无声地改变公民的品行,抚
慰和温暖心灵的伤痛,让人性更美好,让这个世界更美
好。
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这个
民族才有希望。文学就是防止世人都成为一个娱乐至
死的物种,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
不开文学。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在他出版的《中国梦》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解决好中国信仰的问题,那么
你就很难在竞争中得到金牌。因为信仰是国家的核心
竞争力,是国家的灵魂。”文学信仰对一个作家同等重
要,如何在乱花迷眼、万象辐辏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祛浮
躁、降虚火、练内功成为考量作家优秀与否的标准。一
个称职的作家应该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坚持正确的创
作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
文学创作好比种庄稼,有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有
的则欠收,甚至颗粒无收。刨除自然条件,方法及勤劳
与否至关重要,创作的情形与作品的成色,是衡量作家
成长与进步的最好佐证。
我下过井,对煤矿情有独钟,并努力做一个煤矿的
“言说者”。文学创作如同煤矿的开采,打眼放炮后攒出
的有煤炭,有矸石,良莠不齐,关键要有一双慧眼。正如
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生必有灭一样,煤矿的遗迹将随着
工业革命的消亡也会了无痕迹,我的责任是尽可能延续
这一过程,并力争让“煤城往事”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以至“怆然而涕下”。煤矿的明
天必定沦落为废墟之美,俨如古罗马斗兽场,区别是一个
地上一个地下,如何培养人们对废墟的审美意识,积极保
护煤矿的废墟,补上废墟文化和废墟美学阙如这一课,是
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
辽源因煤立市,乌金一度成为辽源的符号和图腾,
但随着资源枯竭的临近,曾经的荣光黯然失色,转身后
的辽源与煤炭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临花
自照,遥遥相望的状态。我的非虚构长篇散文写作,从
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就是翻捡和捋顺辽源昨天的来龙
去脉,让渐趋模糊的历史增加清晰度,每一独立成篇的
散文都是一粒珍珠,用时光这根线连缀起来,就是一条
完整的项链,上面映现的娑婆世相与故事肌理,正是辽
源的前世。因为历史的真相经常需要借助于文学的真
实来表述,文学也有义务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
当辽源历史被我的笔锋挑开一角的时候,蓦然发
现,这座百年小城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历史当然
需要记录,罪行当然需要清算,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探究
是历史为何会出现矿工墓。对辽源这部苦难志的书
写,每一篇都含有一份对于历史的探究意味,甚或以一
种近乎“考古式”的审慎态度,形成了对一座城市前世
的刻写,也成为对那群身处井下,被历史有意无意遮
蔽,又在时间的烟尘中湮灭的矿工的再挖掘,让自己的
作品具备更多的质感和深度,让自己的文字尽量展示
出非凡的洞察力,不断尝试和接近,接近我笔下的真
实,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挖掘出被遗忘的事情,连接
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对东北沦陷
时期西安煤矿的非虚构系列抒写,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
文献性统一,力争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80多年前的苦
难岁月渐行渐远,历史深处传来的不止是一声叹息。铭
记辽源苦难的过去,反刍日寇留给这座城市无法抹去的
记忆与伤痛,“静思往事,如在眼底”。历史的真相往往隐
藏在一个个细节里,我的写作就是挖掘出这些细节,还历
史本来面目,让后人记住黑暗和罪恶并远离,使每一篇作
品都具备信史品质。
这部长篇非虚构散文,书写的疆域正在逐渐被拓
宽,触角正在进一步延伸,看似形虽“散”去,实则神却依
然聚集,每一个独立成篇的个体都从一个基点荡漾开
去,扩散成一环套一环的涟漪,映现出历史的波光,通过
一幅幅近代矿山“浮世绘”,既是对辽源人集体性格的记
录,也是对辽源近代历史的记录。作为一个冷静的历史
叙述者,去探寻隐藏在历史兴衰成败秘密中的一个个断
层,为辽源这座城市留下一部“史记”,鉴古烛今,警钟长
鸣,更好地面向未来。
毋庸置疑,新时代的文学会更加神圣,我与文学的
厮守必将伴随终身,相看两不厌。立春快到了,我似乎
已嗅到了泥土散发出的芳香,为了秋后粮仓的丰足,我
已兴奋地举起了文学的镢头。
新时代:文学更加神圣□王德林
新新写写实实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小微王小微
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总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是看到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去又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徐连云
祝福,还是祝福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
又一个春节,带着固有的韵律,即将翩然而至。
是的,冬已深,春已近。寒来暑往又一年。
感谢作者朋友倾心支持,鼎力相助;
感谢读者朋友痴心喜爱,真诚冀望。
好运连连,好梦圆圆!
——《吉林日报·东北风》周刊编辑部
《蝶恋花》李清照萧 汉 书
杨懋森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