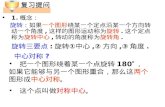责任编辑 吴险峰 唯恐忘却的纪念2018/12/21 ·...
Transcript of 责任编辑 吴险峰 唯恐忘却的纪念2018/12/21 ·...

8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险峰 古华风
本报地址:奉贤区南桥镇环城东路383号丽洲大厦26楼 电话:67110518(办公室) 67110519(传真) 发行67110518 邮编:201499 奉贤报印务照排 电话:67110518 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
1983 年 9 月,我入新寺中学读高中。第二学年起,我们这一级学生按文理分成两个班,由杨淼先生教语文直至毕业。我因为是语文课代表,亲炙先生的教诲比其他同学自然多一些。
其时,先生四十开外,身材英挺,气度儒雅。因其诗文书画早已名动乡野,我们在受教之前即“心向往之”。先生日常的语文课极平朴,内容思想、段落结构、语法修辞……他开门见山,清清楚楚地讲,我们如沐春风,安安静静地听。有时也让我们自修,自己坐在讲台边,或批阅作文,或手持一本线装书静穆地看。觉察分神发呆的学生多了,便说一句:“锄头柄又撑起来了。”(意指人民公社时集体劳动,每有路人走过,农民便撑起锄头看,出工不出力。)同学们知道这是先生温婉的批评,就摄住心神,回到课业上。
进入高二以后,写议论文多起来,先生出题有时极活泼。一次他提早五分钟进课堂,拿起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画,寥寥几笔勾勒,一幅漫画告成:两个人并坐一凳吹笛子,一个人按眼儿,一个人吹,神态俨然发噱。先生要求同学们根据画意,做一篇议论文。那篇作文论了什么、怎么论的我早已忘记,但牢牢地记住了那幅画。后来我在学校图书室翻到一本漫画集,看到华君武的《科学分工?》时,马上想到先生在黑板上摹画之酷似,隐去漫画标题而使学生思维自由之用心,我如醍醐灌顶。
我们这一级中写作较好的十几位学生,被先生选入学校《浅草》文学社,指导我们读些课外书,有时外出采风。当时刻印全靠铁笔、钢板、蜡纸,极为不便,先生就教我们做手写报。我们从学校文印室领几张8开大小的纸,用铅笔浅浅划线排版,空开报头,把先生选定的同学习作誊写好,然后由我拿到办公室交先生看。不管我们做得如何粗头乱服,先生总是莞尔一笑,通览一遍后,旋开一支普通的钢笔,在报头处,沿着“浅草”二字笔画的外沿以细线钩出空心字,或魏碑、或隶书、或楷书,墨线如铁,一气呵成。有些同学看到了羡慕得紧,也自做手写报,取名“晨钟”“春霞”之类,其实单为了哄得先生的空心字,一旦得逞,就欢欢喜喜地剪下报头珍藏,其余部分如何灭失了,他们是不关心的。
我大学毕业以后,也做了语文教师,在几个乡镇中学辗转。其时先生已调入奉贤中学任教,偶见他的杂文刊载于《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就细细读过,其余没有联系。1997年,我也调入奉贤中学,与先生成了同事,但我依旧只认自己是他的学生,早晚请益。先生依然静气儒雅,一有闲暇就看线装书,我猜这些书应该是他后来《红楼撷趣》《历史七读》等几部著述的养料。但先生又是出古如今的,当时同办公室的青年教师中有一件赏心乐事,就是谁最先读到杨先生发表的杂文,如《奴才式破坏》《毋须自卑》《“娜拉走后怎样”》……刻画世相、针砭时弊,或峻切、或幽默,常常一语道破人们心中的迷雾。
2000 年前后,上海并行两套语文教材,我们用的是“S版”。其中编录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带有金圣叹评点,因为备课时深感棘手,教研组便请杨先生上一堂公开课。尽管临近退休,但先生欣然领命。他从“哭庙案”引出,让听课的师生了解金圣叹其人;再讲金圣叹为什么腰斩《水浒》,认为其对《水浒》不同版本整理润色,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的探索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后以课文为例,让学生找出眉批、夹注、尾批各自侧重的评点内容,从草灰蛇线中体会“风雪”的环境渲染,林冲被“逼”的跌宕起伏,领悟金圣叹评点《水浒》对后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深刻启示。
这是我听的杨淼先生的最后一课,至今回想,依旧如沐春风。
(作者为杨淼先生学生,现任致远中学党支部书记)
□ 汤朔梅
每年冬至前一天,是杨淼先生的忌日。而今年12月21日正值他去世五周年。入冬,曾在报社提及此事,朋友说,那就搞一个纪念专版,杨先生是我们敬重的学人。于是搜辑他生前的照片、墨宝、出版的著作、文章,这在我则是当仁不让。
五年后的今天,再来纪念他,我以为有以下的意义。首先,国人在兜了一个圈子后,重拾传统文化。而杨先生则是一个一贯重视传统文化的人,无须赘述,他深厚的传统学养及他的著述很能证明这一点。其次,他是一个读书人。终其一生,他以读书、教书为安身立命之本。而读书成了他一生的嗜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是充实提升自己;为人者,只是标榜给他人看。杨淼先生显然前者。相比于以读书为敲门砖,以读书为博取功名的阶梯者,境界判然。
12月 21日是一个日期,更是个数字。杨先生去世后,我忽然感觉他一生与此有渊源。他在市区的家门牌号是 21 弄 12号,他去世前的病床是21床,他安厝的墓穴也是21号。我猜度他一生中肯定还有不少与这数字有关的几率,只是他自己也没参悟。
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缅怀他,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杨淼学生,现任奉贤区作家协会主席)
前些日子,广东增城的一则关于荔枝的新闻着实在社会上轰动了一阵。一颗叫做什么“挂绿”的荔枝,居然在拍卖会上拍出了 5 万多元的天价。这本来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想当年杨贵妃也是一位荔枝的爱好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百年来受尽了人们的唾骂。可是用驿马传送到华清宫的岭南荔枝,大概还不值这个价吧?贵妃挨骂,其实都是诗人杜牧闯的祸。吃几颗新鲜荔枝,动用几匹驿马,想来也不至于对国计民生产生多大影响。这也可以算古代的一种炒作。现在的大款,不要说南方的荔枝,便是澳洲的龙虾、美洲的鲍鱼,也照样可以须臾之间有空运得来。无论是一掷千金的买家,还是吃遍了天下珍味的大款,都证明了今人远胜古人的道理。
不仅如此,令古人望尘莫及的还有一件事。譬如孝道,这本来是古人的强项。“二十四孝”上有“卧冰求鲤”“黄香扇枕”,也有
“陆绩怀桔”“老莱娱亲”,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佳话。但所有这些个古之孝子有个共同点,便是行孝不怎么花钱。你看,一条鲤鱼、几颗橘子,能值几何?至于黄香、老莱子他们,简直一文不花,照样博得“孝子”的美名。这回用几万元拍得一颗荔枝的买主,据说也是一位孝子。他把这颗身价不菲的荔枝奉献给了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吞下这颗荔枝时,高兴的表示,她是“赶上了
好世道”,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情景倒是有味的,但是这种孝道,价格未免过于昂贵了些,非常人能够问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当一个古代的孝子,要比今天容易的多。所以我以为相当孝子的今之众人,还是厚古薄今一点为好。尽管今之孝子在排场方面,胜过古人已经不可以道里计。
我记得过去与一句谚语:“孝则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淫则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这话虽然俚俗,却包含一定的哲理。当然孝顺归根结底还是要用“迹”即是行动表现出来,不能永远藏在心里。但衡量孝道的深浅,却显然不能以花钱多少为准绳。汉高祖刘邦,本算不上一个懂得孝道的人。楚汉相争的时候西楚霸王
项羽抓住他的老子当人质,挟迫他做出让步。但刘邦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反倒对项羽说,当初你我曾结为兄弟,我爸就是你爸。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你爸”,那就请分我一杯羹。可谓无赖之极。后来他当上了皇帝,突然又起了孝心。因为太公思乡心切,他竟然在首都长安附近,“克隆”了一座老家一模一样的“家乡”,并将老家的村民鸡犬也统统迁来此地,以表孝心。这难道真的是孝心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摆阔而已。
“孝”这个东西,我们自然还是要批判地继承的。像买来高价荔枝敬奉母亲的那样事,社会效果不见得好,恐怕只能适可而止,下不为例的为好。最让人看不懂的是,有些人常常要把一些本来平常的事做得变了形。要么是将年迈的父母赶出家门,任其流落街头,或是为少许几个赡养费而举家闹上法庭;要么却在父母死后不吝花费,办丧事、购坟地、修造豪华“阴宅”,甚至连阴间的“三陪女”都考虑周到,一并烧化。什么事情到了这些人手里,总是要走上邪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古人的孝道或许也有其虚伪的一面,但那些在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生活细节之中,负一袋米、递一把扇、留一颗柑橘……不事铺张,持之以恒。更没有炫耀和炒作。也许这些才是我们应该真正继承下来的东西。
(本文发表于2001年8月21日《解放日报·朝花》)
荔枝与孝道□ 杨 淼
(著名画家季仁葵为好友杨淼先生生前所作个人画像)
如沐春风
□何建祖唯恐忘却的纪念
下图为杨淼先生生前创作出版书籍、文学笔记、手抄本和杂志、书刊
杨淼先生生前所在学校留影
杨淼,字江号(1940.10.2—2013.12.21)祖籍安庆,生于上海。1960年秋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旋来柘林中学。后于陆家小学、道院中学、新寺中学、奉贤中学任教职。是奉贤第一批高级教师。其学养深厚,文史哲、古今中外兼通。上海市作协会员,创作面宽泛,尤以杂文名世。
人物小记〉〉〉
(本版策划:潘玉明)